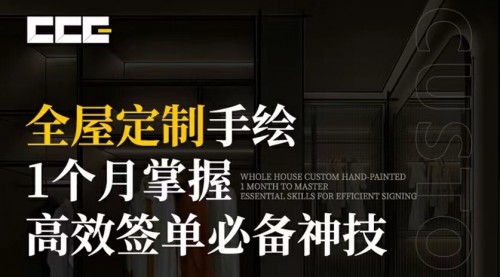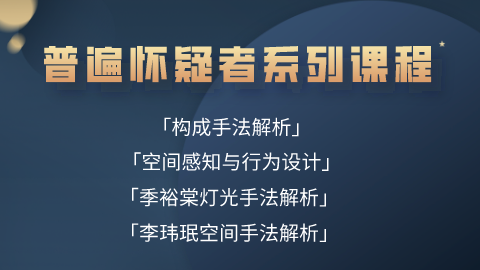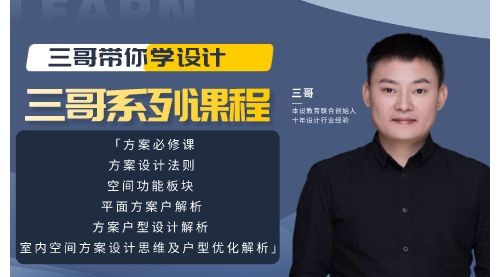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奥北之家家居 于 2015-6-16 12:54 编辑
最早出现房子的时候,人们只是把房子当做是遮风挡雨的处所,而随着与时俱进现在的人都具有了一定的审美功能。而且现在的房子不再是以平房为主而是以高层为主,审美品位趣向的上升在社会中日益明朗,着意“雅趣”的文人居室追求和创造了一种悠然恬静的超脱美。
山林乡野——文人择居的首选之地
文人居室之‘雅’首先指向山林乡野。这一文化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返归自然’的老庄哲学,然而,它现实的衍生为一种风尚,则不能不归功于魏晋的高隐之士。
魏晋是一个一元破碎的时代,社会大动乱的狰狞,传统儒学的苍白与暗淡,将文人纷纷导向山林,隐逸之风遂大事流行。在陆机、左思、陶渊明的笔下,山林溪谷的隐逸生活充满优雅的情韵:好似高歌入云的楼阁;浓密的树叶隐蔽遮掩,如同翠绿凉爽的帷帐。清风吹拂秀木,白云缭绕山岗,红花辉映向阳的树林,清泉奏出悦耳的音响。居于如此恬淡静谧之境,以松菊为友,与琴书为伴,远胜于朱门的富贵与喧嚣的俗韵。自魏晋以降,以陶渊明隐居生活为典范,山居、村居、野居、郊居成为一代代文人孜孜以求的居住方式,也成为他们不倦吟哦的题目。
宋 梁楷 东篱高士图 明 周臣 水亭清兴图
在文人雅士的观念中,山林乡野具有多层面的雅的气韵。“野外罕人事 穹苍寡輪鞅”。“世上事如许 山中人不知”。对于淡泊功名心、力求遗忘纷繁险恶现实的文人来说,甩落俗情,远离尘世纷扰是山林乡野至关重要的文化品性。居于斯,既可得“青山当户 流水左右”的怡然之乐,又可在“柴荆偿自闭 ”“园林深似隐”中割断与尘世利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村居之居并非意味着排除一切社会交往,但在这样的环境中,除故友偶过相访外,与之交往的大致只有野老和山僧,前者虽泛文化教养却质朴浑厚,后者身在空门,绝尘离俗。隐居文人与他们交往往往还大为是平和的、净化的,不复有锱铢利害相磨压的使人心悸的利益冲突。在“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的淡然相处中,在说禅参悟、品茗弈棋的虚静心境中,文人的心神盎然适意,悠然自得。
元 王蒙 溪山高逸图局部
而且对于文人来说,山居、村居或乡居更可以复归自然。筑舍于幽山深谷,“山蔚蓝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为台”。“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屋舍与繁复轮回而又单纯剔透的自然宇宙浑为一体,化为山水幽韵中的一段静默旋律。这样一种浑然无迹的审美意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与天壤俱 闲随云舒卷”,从而在“起望山光 寻昧道腴”中实现无穷宇宙与自身心灵世界的淡泊无间,“虽鄙衣恶食不知也”。
元 任仁发 横琴高士图
恬淡、素朴、远离名利而与大自然同生共息,栖息于这样一个境界中,文人士大夫“或隐居以求其志,或趋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在这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理想的破灭在这里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文人的心神不再绷得紧紧的去防戒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虞之祸与险恶的倾轧,而是浸润于闲适悠然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山林乡野之居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其间自然有层次可分。文正亨《长物志》言:“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与自然山水的亲和关系即远离尘市的程度,显然是如上区分的内在依据。然而,无论是次之的村居还是又次之的郊居,更遑论最为理想的山水之居,都对文人具有莫大吸引力。又是一种与文人精神气质相淡泊的生活方式,一种令士人追慕不已的审美情调。
宋 李唐 万壑松风图
城市山林——文人居舍新选择
具有独特气质和美的山林乡野是酿造文人士大夫居舍雅气质的绝妙境地。但是,山水之居、村居、乡居毕竟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并非随心所欲便可实现。于是,在士与隐的夹缝中选择一条中间出路,便成为中晚唐以来文人士大夫竭尽全力关注的紧要问题。白居易感应这一精神趋向,提出了著名的“中隐”理论。其精髓乃是既不永绝宦情,又通过对文人生活情趣的全力发掘与精致加工,来强化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在集权机制与文人士大夫独立人格日益激烈的冲突中,取得精妙的平衡。
|

 发表于 2015-6-16 12:50:00
发表于 2015-6-16 12:50:00




 楼主
楼主